https://mp.weixin.qq.com/s/E-RE_NfhyMayldXnrEa8t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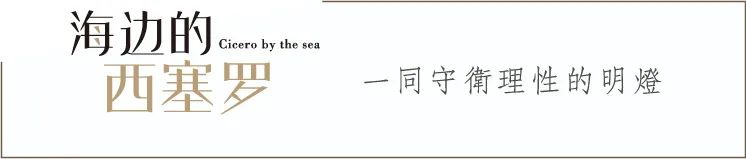
如果说在近代以前,有哪一段历史最让中国人的感到屈辱、不堪回首,那么我想也许非南明史莫属,站在明朝和汉族的角度去看,化用丘吉尔的那句名言:人类史上,从没有这么少的人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征服这么多的人。 
关于满清入关之时一共有多少兵力,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数据记载,按照比较靠谱的推测,当时的满洲总人口不过就两百万左右,再减去老人、妇女、儿童等人,最后的实际兵力也就在9万左右,如果加上蒙古军队,总兵力应该不超过12万人。 反观当时关内的汉族政权,崇祯上吊后的南明,经过征兵等措施后,账面上可是有百万大军的实力。可是就是这样一个一百万打十来万“优势在我”的大好局势,外加山川险阻、夷夏大妨、两百年正统王朝积威等等众多对南明有利的因素,满清入关后对明朝的侵攻、扫荡却如喝凉水一般痛快。 没有东晋的淝水之战、没有南宋的擂鼓战金山,从1644年崇祯皇帝在煤山上吊,到1662年永历皇帝被吴三桂用一根弓弦勒死,南明一共只存在了短短18年,大明死的创纪录的脆生。 
期间,中华大地天下披靡、万民流离、剃发易服、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明朝的军民就像是被驱赶、宰杀的牲畜一样,对入侵者几无抵抗之力,明朝的知识、军事精英则纷纷卖身求荣,毫无气节的投靠“新朝”的怀抱。 这样事情,如果发生在一个如古印度那般没有统一民族精神、不看重现世的荣辱兴亡的、只等着新征服者出现在兴都库什山口就乖乖归顺的民族身上可能也就罢了,毕竟人家不太在乎这个。 可是,中华文明发展到明朝,偏偏是最以“气节”自诩的,有明两百多年,士大夫一直把“忠君爱国”“夷夏大妨”的口号喊的震天响,到了明末,这些口号还成了束缚皇帝自己作出决策的绊脚石——崇祯皇帝之所以在天下糜烂时迟迟不肯作出与满清媾和或者迁都南京的决定,就是因为朝堂上总有人在唱不可割地求和、祖宗社稷不可轻弃的高调。 
这样一个喊了两百多年爱国口号,在内部时刻拿着放大镜找“奸臣”,把任何主张妥协退让者都揪出来当敌人来消灭的“皇明”,怎会在敌人真的打到家门口时“百万义师,一朝卷甲;芟夷斩伐,如草木焉”呢? 才18年啊,这跪的也太快了吧? 这些疑问,是我大学读明史的时候就一直存有的。前两天听说读客文化又重新出版了顾诚先生的名著《南明史》,冒昧的把样书又要来读了一下,有了一些新的感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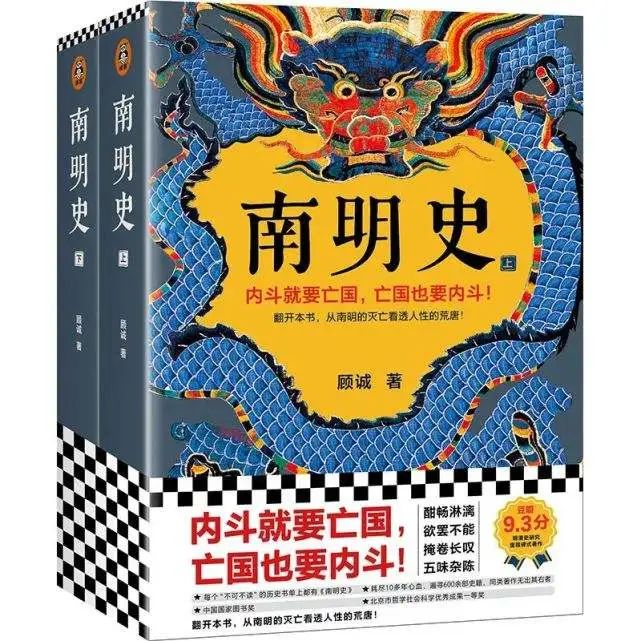
首先说说顾诚先生这个人,很多非历史学的人一听这个名字,往往就往80年代写朦胧诗的那位顾城那里想。其实我们历史学界的这位顾诚先生在成就上丝毫不应亚于文学界的那位。

顾诚先生是北师大的教授,主研明朝历史,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那个特殊年代依然拿出了一系列今天看来颇有价值的史学成就。最著名的一个,我想当属他对李岩的研究,郭沫若写《甲申三百年祭》,花了大量篇幅写这位传说中李自成手下的干将,后来又因为《甲申三百年祭》被领导人定为“全党都要学习”的模范文章,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该文一度成为明史学界不容置疑的研究起点。 可是作为一位严谨治学的历史研究者,顾诚先生偏偏在那个年代对这篇“学术圣经”提出挑战。他在论文《李岩质疑》当中,用严谨的史学证据一步步进行推论,最终提出了“至今未发现一条可以证明李自成之外存在着另一个李公子或李岩的可靠证据”的结论。等于说郭沫若的论述是在无的放矢。 我上学的时候老师曾经评价说,顾诚先生这篇文章相当于明史界的《君士坦丁大帝赠礼的证伪》,而顾诚先生的这个胆量和对史学严谨的态度,由此可见一斑了。 这段对郭沫若的抬杠被收录在了此次出版的《南明史》中,而如果你在往下读,会发现顾诚对郭沫若权威说法的挑战不止于此。 比如《甲申三百年祭》中认为,李自成在进城之后,是因为腐化堕落才丧失民心丢了江山的,此论在上世纪中叶曾经颇为兴盛一时。 香港那边的金庸在小说《碧血剑》里也以此为基础塑造的李自成形象,一个前期豪侠仗义,后期腐败忘本的形象。 
可是顾诚在《南明史》当中,用了一个特别简单的方法就击溃了这个传统观点——他就把李自成从进京到败亡的时间线给大家缕了一遍,“三月十九日大顺军进京,四月初十左右,即得知吴三桂率部叛变回军攻占山海关,十三日晨李自成、刘宗敏亲帅大军离京平叛。”李自成在北京,一共也就住了二十三天的时间,屁股还没把龙椅坐热呢,想腐化能腐化到哪儿去? 顾诚还举了很多王朝腐化、衰落的例子,说明腐败对于一个政权,一定是一个内生于制度的、延续时间漫长的过程。 所以《甲申三百年祭》在这个问题上的立论和结论都是不对的,腐败不是突然发生的,也不会因领袖的个人意志而突然消失,李自成对他的政权能做的事,其实相当有限。 当然,顾诚在该书中重点解谜的,还是南明衰亡的过程,就像我前面提到的那个问题——一个尚带甲百万,掌握中华正统、以气节自诩的王朝,是怎样在异族入侵时秒跪的? 
在顾诚写《南明史》以前,很多史家对南明败亡的论述承袭了清人修明史时的一些观点,把明亡归咎于“忠奸之辩”——明朝之所以亡国,就是因为史可法这样肯壮烈死节的“忠臣”太少了,而马士英、阮大铖这样卖国求荣的奸臣太多了,活活的把大好河山卖给了大清。 这套说辞,当然是老百姓最容易理解的,而清朝作为后继统治王朝,也希望老百姓这样想——毕竟哪个统治者都希望自己治下能多一些陪自己一条路都到黑的忠臣。 
可是顾诚先生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基于史料作了一番非常细致的呈现,比如史可法,他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接任兵部尚书一职,又怎样迫不得已“自请都师江北”,在江北四镇、他看到的四镇兵马是个什么样的状态,最终又是以什么样的心态困守扬州城。而后世又出于什么心态一定要为这位忠臣的军事能力“贴金”,明明只守了一天,却非要说他守了十几天。 在顾诚先生的还原当中,我们可以看出,史可法其实是一个能力不足的垂死王朝的裱糊匠,与传统史学叙事中描述的那个壮怀激烈、主动请缨、对保卫大明、收复河山信心满满、胸怀韬略的“文岳飞”形象不同,史可法在南明历史舞台上的表现,全程都是非常被动的。 “他缺少雄才大略,总想处处应付,八方妥贴,最后落得个事与愿违。”这是顾诚对史可法的总体判断。而看了他的相关论述后,你会赞同他的判断——他忠心也许可嘉,但却是一个不合格的“大明裱糊匠”。 当然,这种能力不足实则并也不怪他自己,自开国以来就防权臣如防贼的大明,从来不会主动培养那种能在危难时刻力挽狂澜的能臣,英宗时土木堡之变,瓦剌军打到北京城下,千年的铁树好不容易开了一次花,出了个能人于谦挽狂澜于既倒,结果下场还那么惨,后世的大明臣子们就更不敢“逾矩”了。 史可法其实也是晚明那种压抑气氛当中在官场上委屈求全的渺小一份子,他性格中的最致命缺陷是被动,缺少祖逖、岳飞那种救国英雄所必须的主动精神。 
只不过在山河倾覆、社稷板荡,中国的传统忠奸叙事要求此时必须抬出一个人来做一做忠臣表率,唱一出“数点梅花亡国泪,二分明月故臣心”的悲歌。而史可法好歹在扬州尝试着守了一下,矬子里拔将军,只能是他了。 再读下去,你会发现就像《南明史》中的“忠臣”没有那么忠勇,而“奸臣”们,似乎也没有传统叙事当中那么可恶,他们其实就是明代有意培养的那种“被动型人格”的另一种体现。与史可法只是一体两面而已。 这里面的突出代表,大约是美女柳如是她老公钱谦益,清军远在天边时,他作为东林领袖,爱国口号也是喊的震天响。好像全天下就他钱某人最爱国。可八旗军的铁骑一到南京城下,这老伙计果断就怂了,剃发、开城、下跪,一气呵成,是汉奸里的英豪。 
从表面看,钱最初的“战狼”与后来的秒跪似乎是两个极端,但在顾诚先生为我们还原的那个南明场景当中,你就能理解他为什么那么干:忠君爱国、华夷之辩这些口号,本来也不是钱谦益这种人自己思想中内生出来的人格理想,跟当时所有能够被明朝那个体制所吸纳的人一样,钱谦益其实也是一个皇权和社会强力说啥是啥的“被动型官僚”。 在清兵没来之时,晚明的主流是袖手高谈忠君爱国,那他钱谦益就也谈,一不小心还因为文辞卓著,混成了东林领袖。可是当清军的屠刀架在脖子上,一种更大的强制力到来时,他顿时就随风倒了。 相比之下,反倒是投降之后,钱谦益倒有了一点发自内心的主动性,多次与残明势力暗通款曲,试图反正,但此时已经晚了——可悲是,在那个年头,像他这样先跟风“爱国”、又跟风投降,活到人生最后才隐约有了一点自觉、却也晚了的人物,并不在少数。 
是的,晚明政局的一个奇葩之处,就在于它的中心被一群典型具有“被动型人格”的人所占据。 无论是抗清的史可法、还是降清的钱谦益,亦或是后来那个被推上皇位、然后一门心思到处逃跑的永历皇帝。他们的性格共同点就是都是极为被动的人,只能被历史大势推着走,而不能也不敢去主动改变形势。让这样一帮人来主持与满清战斗的大局,当然不亡国才怪。 而这种人格如果再堕落一步,就是后来被鲁迅先生所深恶痛绝的那种奴才。 
所以从晚明的士大夫秒跪,到清代的奴才遍地,这个过程其实如德芙一般的丝滑。 那么那个年代,华夏大地上有没有积极主动、愿意主动出击,捍卫自己的内生的人格与理想、护国护民的真英雄呢? 其实也是有的。但你会发现特别奇怪,这种人在那个时代总是被精准的排挤到明朝那套体制的外围、被重重压抑着。 比如壮怀激烈、南明史上唯一真够格当皇帝的隆武帝朱聿键。 
明末乱世中因为主动募兵勤王,他居然被崇祯废为庶人,派锦衣卫把其关进凤阳皇室监狱,苦熬了七年,直到崇祯上吊才勉强捡回一条命。 比如纵横数省、两厥名王、打的清廷闻风丧胆的大将军李定国。 
作为南明史上不可多得的将才,出身居然是“反贼”张献忠的义子干儿,如果不是明朝马上要亡天下,根本不可能给他“反正”的机会。 再比如一度兵临南京城下,后又收复台湾的“民族英雄”郑成功。 
他爹郑芝龙是个常年与朝廷为敌的大海盗,也是在明朝快不行了的时候才被勉强收编。 而郑氏集团高层除了郑成功一人似有志匡扶社稷,他爹他儿子他叔他侄……所有其他人,都是是一帮只求“把郑家家业做大”的精致利己者。 不难发现,以上种种“主动型人格”的人,在明朝体制还能正常运转时,都是体制想要限制、镇压乃至剿灭的“反体制者”。而当这个体制本身无法自保,必须将他们招安、引他们走向舞台中央的时候——非常悲剧的是,时间已经不够这些英雄长成羽翼,挺身抗暴了。 更让人感到喟叹的,是即便明朝这个体制已经朝不保夕,它依然将打压、敌视自身内部的“主动型人格”者作为其第一要务。弘光朝廷的“借虏平寇”、鲁监国与隆武帝的正统之争,都是这种打压思维的表现。当然最狗血、最让人喟叹的,还是逼反孙可望的操作——同样作为一个旧体制边缘的“主动型人格”者,孙可望确实是个人才,只不过跟其干兄弟李定国不一样,他有更多的私心,想让朝廷封自己个秦王当当。按说此时的明王朝,土地都丢的几乎只剩广西和云南了,你就是痛快的封孙可望个秦王又能怎么样?可是不行,明朝的皇权从朱元璋那会儿开始,就是葛朗台般极端吝啬、拒绝分享的。你一个老西营、臭土匪出身,也配姓赵?啊不,也配封一字王?给你个两字王算顶天了!不仅如此,我还要猜忌你,提防你,用皇权的那套“驭臣术”离间你和你兄弟,结果硬生生把这个主动的能臣逼成了贰臣。 说到底,南明的速亡,其实亡于明朝一种主动筛选机制的过于成功——这种筛选总是把被动应命的人挑如它的体系,而将积极主动的人才排挤出去。 为什么会这样,这个憋屈的体系是怎么形成的?
在顾诚先生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南明的病根,其实在明王朝建立之初就落下了。 两百多年前,当朱元璋夺得天下后,这位权力欲极强的皇帝,为了让子孙世世代代坐稳江山,订立了一套非常不近情理的“祖宗之法”,他鼓励、甚至强行要求他的臣子、百姓们必须“忠君爱国”,且这种“忠”和“爱”的方式,必须由他自己来定义,臣子百姓在这个体系中只是被动接受的客体,你们没有主动发挥的权利,遵旨办理就可以了。

中国儒家思想十分强调“忠君爱国”,但至少在孔子和孟子的时代,这种“忠”和“爱”是有条件的,允许臣与子保留自己的判断力和主动性。 比如说孔子虽然曾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他的意思原本很可能是“只有君有了君当有的样子,臣才能相对的有臣该有的样子。”强调君臣义务的对应性。 孟子在这一点上就做了集中阐发,他阐述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孟子强调君主只有爱民才能要求臣民忠诚,如果君主不把臣民当人看,臣民则有权利推翻他——这就是强调臣与子对君与父的爱,应该是活泼、主动、有自己判断的。
可是这样的阐述,让权力狂朱元璋非常恼火,他不允许臣子对他的忠诚是讲条件的——君主贤明你们就爱,不贤明你们就不爱,万一我子孙后代有个“不贤”的,岂不是反天了吗? 所以朱元璋要垄断对忠孝的定义,他将孟子移出孔庙,还下令删除《孟子》中不合时宜的章节和言论,比如《尽心篇》中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万章篇》中的:“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以及《离娄》篇中的:“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等等等等…… 而朱元璋对明朝臣民的设计也完全是“被动式”的。在朝堂,取仕的八股完全是代圣人(实则是皇帝)立言,官员的一举一动全在锦衣卫的监控下。而在民间,老百姓没有路引就不能出县,甚至所从事的各个职业也必须代代相传,你在明朝初年掏大粪,到了明朝末年你第N代孙理论上说也必须掏大粪,不考公务员(科举)就没有换工作的指望。 这个被动式的体系,经由他儿子明成祖朱棣的进一步改良,变得更为变态而令人讶异——如果说朱元璋是把臣民都当成了植物,栽在地里不许动窝,那么靠靖难之役上位的朱棣,就是把皇亲国戚也当成猪来圈养。厚其禄而削其权,圈在地方王府里,除了生孩子,什么也不许你干。朱姓皇族们只有在王府里吃饭睡觉玩女人作威作福的作恶权,想干点利国利民的实事,基本门都没有。 所有这些动作,都是为了最大限度的打压、削弱除皇帝以外所有人的主动性,然后再通过帝国体系对臣民进行反复的、填鸭式的忠君爱国教育。 明代这一点做的确实是非常成功的,一直到明末,帝国舞台中央所剩下的都是一群没有自己主见、只能循规蹈矩、一切循规办事的“被动型人格者”,“主动型人格”的人则被排挤、被圈禁甚至被逼反,游荡在社会边缘。而这个被动型社会因为不断接受皇权的要求,应激性的不断做出“忠君爱国”的反馈,看似民气十分可用。 但问题在于,这种驯化过于成功了。 当突然有一天,皇帝在煤山上上吊了,那个强行要求臣民们该怎么忠君、怎么爱国的“主人”不存在了,于是进入了一种“天下失主”的状态。这个时候人们才发现,由于皇权有意选拔了太多“被动性官僚”在自己周边,拥有“主动型人格”的人在天下巨变中有没有足够的时间进入中心,进入了也不会怎样完成权力的分割与妥协。这个民族进入了一种茫然无措、束手待毙的可耻状态。最终在外族的入侵中亡国、亡天下。 所以,南明之亡,是谁之过呢? 冶金学上有个专业词汇,叫“金属疲劳”,指金属构件在外力的不断扭曲下内部不断积累损伤,最终发生脆断。 我想,其实南明的故事,也是一个“金属疲劳”的故事,在孔孟时代,中国人曾有一种活泼的、主动的、坚韧的忠爱本能,但终明一代,皇权不断的在用强力反复扭曲、弯折这个本能,皇权告诉你,这样忠,必须这样爱。最终,就像被扭曲、弯折了无数次的轴承一样,这种“忠君爱国”的精神,在最需要其发挥作用时脆断了,在外族的铁蹄与屠刀面前,亿万万人齐束手,竟无一个是男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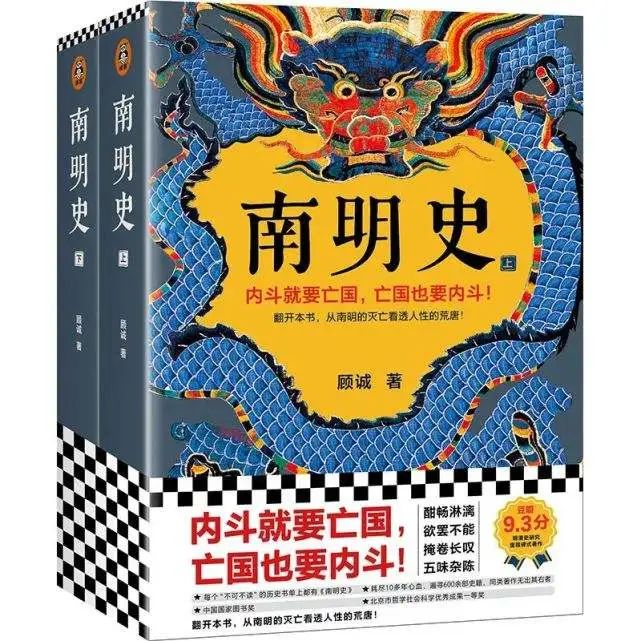
这,就是顾诚先生的《南明史》为我们讲述的悲剧。感谢读客文化将这本书推荐给我,我也将它推荐给大家。这是我近期读到的难得的一本好书,它会让你掩卷深思,喟然长叹。 全文完
本文6500字,感谢读完,好久没推荐书了,这套书我蛮喜欢的,许久不做的书评,就是这样,长文不易,喜欢请三连,多谢了。 
在异族的铁蹄践踏之前,皇权早已拗断了这个民族的精神脊梁。
各位好,时事这几天写累了,今天更一期书评。
1
2
3